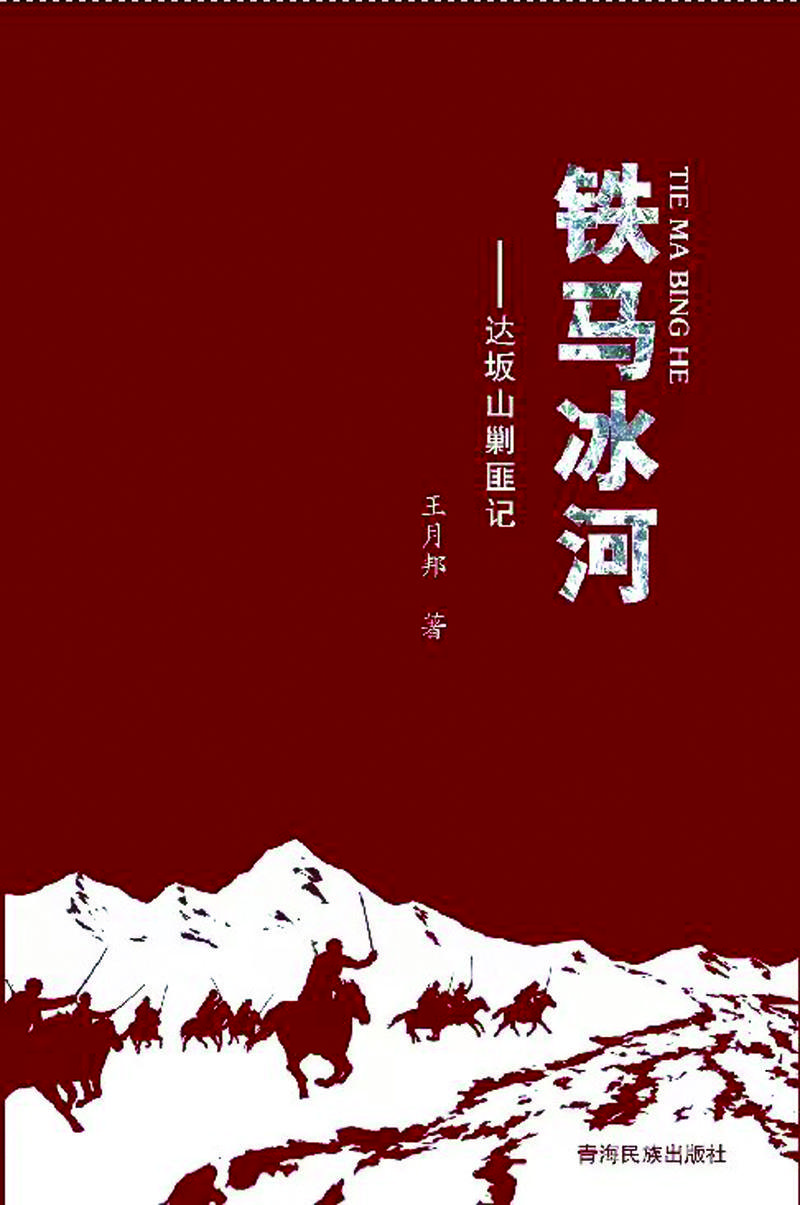
□刘大伟
有着地质勘探技术和司法审判经验的月邦先生业余从事小说创作,这事本无稀奇之处,因为文学创作并无专业限制,然而貌似寻常的事情往往又隐含着不同寻常之处——月邦先生似乎只写长篇小说,而且只写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这也意味着,作家要把那些带有结论性的、标本性和封存在档案袋里的史实加以形象化、小说化,并赋予其美学的“综合性”,这种写作任务的艰巨性犹如推着巨石上山,然而当他接连完成两部长篇历史小说时,作为读者的我不免感到惊讶了:他是怎么做到的?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的小说创作数量相当可观,几乎每年都有三千部左右的长篇问世,如此庞大的小说体量中,取材历史的长篇小说比重并不占优,与文学关联着的历史往往是被“穿越”或“戏说”了的“往事”,网络写手们对历史的解构乐趣远远超过了建构的意义。这里面有一个重点,那就是作家的历史观问题——作家如何认识一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思潮对现实的推进和建设功能,包括对人的影响和塑造,对价值的取舍和选择,对精神的探寻与传递。历史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当它以基本素材的面貌进入小说“创作流程”之后,作家如何通过合理的想象和虚构,营造出艺术的真实,最终实现主体所理解和表达的那种历史真实和审美高度,这的确是一件难度不小的事情。
毋庸置疑,《铁马冰河》给人以一种强烈的真实感,不是说剿匪这段历史没有经过作家大脑的过滤,而是说月邦先生的“滤镜”比较高级,它熔铸了作家开阔的历史观和纯然的艺术感,随着小说的完稿,作者将这种“看不见”的难度成功转化成了“掂得住”的厚度。当然,难度不仅于此。长篇小说开头部分往往因灵感的到来和准备的充分而不会觉得太难,真正的困难是在“继续”这个层面,也就是说作家每天坐到桌子前,如何把前一天写成的内容续写下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经受多种因素的干扰和考验。这里面最大的考验来自作家自身,即作家对持续推进的这部作品是否充满信心,材料是否齐备,时间是否充裕,思考是否成熟,结构是否清晰……还有一个关键因素:体力能否保证?每一个要素都是关键环节,任何一环出现问题都会对正在进行的创作构成重大影响。
一个严肃而颇有意思的现象是:青海作家诗人善饮,尤以互助作家群为甚。每隔十天半月,这些多巴胺无比旺盛的“酒徒”们定要寻找一个由头,或相聚土乡,或啸吟西宁,美酒与诗,好不痛快。我也非常了解互助作家兼酒家们捉笔和豪饮的功夫个个了得,但大醉过后没有一天半宿,身体确实难以恢复常态,更别说坐到书桌前继续写作了。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挑战。可喜的是,月邦先生在大部分情况下都能战胜自己,在别人推杯换盏的夜里,他却埋头于书房,穿梭于笔下各色人物之间,直至这部小说最后敲定,他才要谋划一场雅聚,意在弥补长时间的蜗居带来的某种缺憾。
就长篇小说文本而言,最大的难度在于结构。文本的深度和宽度与小说结构的搭建不无关系,犹如木匠师傅盖房,梁柱几尺檩条几根,直接决定了房子的间架结构和空间大小。木匠对房屋结构的把握是一个定数,一旦确定下来不再更改,小说家的文本结构却显“活套”,虽有初步的设定,然而随着小说的不断推进,人物命运的意外转折,其结构可能会随之发生变动。故此,作家需要在变与不变的文本框架中持续写作,既不能过于单一,也忌讳过于芜杂。《铁马冰河》的文本结构给人的整体印象是明晰、紧致、干净。小说以再现的笔法,讲述了青海解放前夕至新中国成立后三年期间,互助及其邻县大通、门源等地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剿灭匪患而不懈努力,奉献青春乃至生命的革命故事。故事主线以青年才俊徐青岭为中心,叙述了剿匪队伍从无到有,密切联系群众后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辅线以土匪头子鲁国佐、鲁顺德为代表,描述了国民党残部纠集反动势力,向新生的人民政权疯狂反扑、荼毒群众直至走向覆灭的最终结局。两条线互为交织,演绎出了与剿匪历史密切相关的党政机关、地方武装、普通百姓、商旅脚户和土匪恶霸等众生群像的悲欢离合与复杂世情。小说对每一件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诸多事件彼此叠合而产生的新的走势叙述得清晰而又节制,这样的结构方式似乎为阅读的进行做好了准备——如果阅读是一种漫游,那么《铁马冰河》无疑为读者的漫游之旅铺设了一条干净的路径,读者尽可循着故事的跌转和人物的命运不断前行,沿路没有干扰因素出现,阅读目标明晰而畅达,有丰富阅读经验的人完全可以做到一口气读完。此外,文本略有古代章回小说的某种印记,体例上虽没有明示,每章末尾却隐含了“且听下回分解”的余韵,不断吸引读者想快速读下去,从而走进“他到底怎么了”的期待视野。
毋庸置疑,这部小说塑造的人物众多,人物关系与事件关联极其复杂,而这种复杂性恰恰就是让小说文本绵密厚实起来的基本要素。因为有很多纪实的成分在里面,作品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与凸显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行为方式来实现,情感与心理的表达比较省略,这可以理解。小说写到了青岭与朵儿的恋情,这一关系不仅仅是爱情意蕴的传达,它也隐含了普通民众的婚姻观、价值观等问题。我在阅读过程中一直关注着朵儿这条“枝蔓”,生怕一不小心就会错过什么,然而作家的笔墨过于节省,“为什么不多写两笔”成了读者心头的疑惑。或许,这正是作家采取的一种高明手法——吊足你的胃口,转而叙述其他。不管怎么讲,我还是期待“拔出萝卜带出泥”的那种粗粝与质感。平心而论,有着五十个章节的《铁马冰河》,其体量与规模确实很大,为了让其结构清晰,作者进行大量删减的可能性显然存在,我倒是有这样一种设想:读完精简版的《铁马冰河》,再去读未删版,哪一种体验会更吸引人呢?
当然,这样的删减也带来了语言方面的洗练与老辣。不得不说,当下很多长篇小说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语言不够凝练,废话较多,无意义的表达拆解了小说语言应有的张力。我不知道月邦先生是否有过写诗的体验,但从一些出自其手的歌词判断,他应该有过类似的语言训练,不然在推进长篇时难以做到始终如一的精准与洗练。整体而言,《铁马冰河》的语言生动节制,有嚼劲,有意味,特别是人物语言非常贴合人物的身份及其生活场域,行话、方言和富含民俗文化与地方传统的语言系统为河湟文学矿脉的进一步开掘提供了重要的范式。
评论家孟繁华在谈及近二十年来长篇小说的基本样貌时提出,文学没有青春人物是不可想象的,从新文学肇始的“青年”和“新青年”开始,百年中国文学一直矗立着青年形象,但近十年来,我们似乎还没有看到有光彩的青春文学人物。无可争议的是,《铁马冰河》为河湟文学贡献了一个极富时代气息的青春形象,这个典型形象就是出生于南原的青年才俊徐青岭。作为茂源公司的脚户,他行事稳健,讲义气,有胆识;加入剿匪队伍后更显男儿本色,有远见,有担当,且身手不凡;与人交往时,他又是一个知书达理、干练、重情的好小伙。就我有限的阅读经验来说,河湟文学中多有父亲母亲、民族英雄、军队将领和村镇干部等典型人物的塑造,“有光彩的青春人物”的确并不多见,徐青岭的出现无疑为近二十多年来的河湟文学弥补了这一典型人物的空缺。此外,小说对土匪头子鲁顺德、鲁国佐两位反面人物的塑造亦很成功,着墨不多的杨瑁、谢掌柜、青坡、青草、朵儿、文思问、陈得寿等次要人物亦形象生动,令人难忘。读者可从这些小人物身上窥见自己内心的渴望与冲动、快乐与悲哀,以及面对艰难险阻时个体的犹豫与徘徊,坚持与挣扎,这实际上是透过史实和档案材料的云层,让“人的文学”落到实处的一种朴素创作。
如果说“历史就是一种叙事”,那么《铁马冰河》的叙事主体就是平凡的小人物,尤其在河湟地区,他们代表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存在的复杂性。这部小说虽有取材上的宏阔特点,但在创作过程中,作家努力让小说文本从宏大叙事回归到了“人”本身,更加关注普通人的生命经验和成长认知,这样的理解和书写无疑是具有一定人性深度的创作——如同作家在生活的硬纸板上抠开了一个艺术的孔洞,借着人性的光辉,所有历史的波澜、存在的必然与事件的偶然都在小说的白纸上渐次成像,只因观察视角不同,所成之像的大小明暗也各有差别。另外,开放式的小说结尾也为主人公的命运走势打开了可供想象的艺术空间,穿越这一空间,读者亦可感到一个值得期待的时代已经到来。



